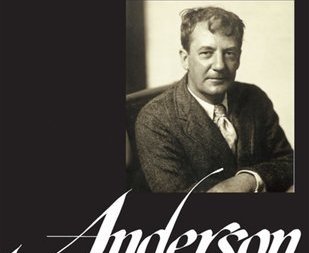安德森的《林中之死》
安德森《林中之死》的元小说特征
封一函
文学批评家们通常都极为关注文学艺术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被福克纳誉为“当代美国作家之父和美国文学传统之先驱”的舍伍德.安德森(Sherwood Anderson)就是这样一位既不满足于对现实的表现,也不满足于自然主义作家所崇尚的宿命论主题的杰出的现代派小说家。安德森在他的A Story Teller’s Story (1924)一书中对当时美国短篇小说的倾向发出了感叹,他批评了这样一种观点,即故事必须围绕情节展开,必须具备道德价值,能“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准”或“造就良民”。安德森所追求的是某种形式,是一种更难以捉摸,也更难以得到的东西。我们甚至可以说安德森在“形式”(form)方面所作的大量尝试,特别是被视为同时代最具穿透力的短篇小说“林中之死”确立了他在美国现代短篇小说史中的先导地位。
原载《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
选段
![]() 形式主义批评家们认为,艺术创造的外在形式甚至可以比艺术的表现内容具有更重要的价值,这用来指“林中之死”尤为适合。阅读这篇以乡村生活为背景的故事,给读者的第一印象是安德森刻意追求的简明性同时体现在语言和情节中。但如果把语言的简明性解释为比刻意和难以捉摸的表达更具有永恒意义和更易令人思考,这是毫不为过的。这并非是要把简明性神秘化。德里达(Derrida)在他的后现代主义经典Grammatology中指出,在“写作中回避”是为了更好地“表现自身”。事实上当这种着意的回避以更为永恒和更具有哲理性的简明形式出现时,也就更带有危险性和目的性,它再也不是简单情感的简单表达。
形式主义批评家们认为,艺术创造的外在形式甚至可以比艺术的表现内容具有更重要的价值,这用来指“林中之死”尤为适合。阅读这篇以乡村生活为背景的故事,给读者的第一印象是安德森刻意追求的简明性同时体现在语言和情节中。但如果把语言的简明性解释为比刻意和难以捉摸的表达更具有永恒意义和更易令人思考,这是毫不为过的。这并非是要把简明性神秘化。德里达(Derrida)在他的后现代主义经典Grammatology中指出,在“写作中回避”是为了更好地“表现自身”。事实上当这种着意的回避以更为永恒和更具有哲理性的简明形式出现时,也就更带有危险性和目的性,它再也不是简单情感的简单表达。
![]() 我们可以把“林中之死”归于心理类或寓意类小说,进而会对作品寓意的确定性提出疑问。按照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任何人想在文字表达中找到单一和正确的寓意只会被束缚于“对”与“错”、“正确”与“不正确”的对立理解中。换句话说,文字表述不区分“A”和“B”,而只区分“A”和“Not-A”,强调“A”和“Not-A”之间的关系和差异。“林中之死”的价值似乎在于寓意的魔力,但与产生这种寓意的形式所具有的魔力相比就微不足道了。神秘的寓意和魔幻般的形式并不对立,它们相互取代,相互掩盖,又相互依赖。
我们可以把“林中之死”归于心理类或寓意类小说,进而会对作品寓意的确定性提出疑问。按照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任何人想在文字表达中找到单一和正确的寓意只会被束缚于“对”与“错”、“正确”与“不正确”的对立理解中。换句话说,文字表述不区分“A”和“B”,而只区分“A”和“Not-A”,强调“A”和“Not-A”之间的关系和差异。“林中之死”的价值似乎在于寓意的魔力,但与产生这种寓意的形式所具有的魔力相比就微不足道了。神秘的寓意和魔幻般的形式并不对立,它们相互取代,相互掩盖,又相互依赖。
![]() 故事中的现实渐渐地“熔合”,最后达到故事的结束,即自身“形式”的显现。这就是叙事者在故事末尾所说的“一件完整的事物有其自身的美”,更确切地说有其自身存在的价值。安德森在他的一封信中谈到了所谓的形式:“我觉得所有从事艺术实践的人都以不惜追求秩序为开始。我们想把某种东西带进意识中来,这种东西总是存在着,可又总是捉摸不到……我深信就形式而言,在很大程度上是个深层的感觉问题”。显然,只有创造该故事潜在意义的叙述人能体会到这种过程。正是通过这一过程,叙述人吸取了现实中的格里姆斯和她所象征的理想美的某些方面,他最后显露出自己是艺术家。这位躺在雪地里的女人在当时在场的男人们眼里成了“美丽的少女”。但毫无疑问,发现这个女人的身体并不是整个过程的结束,这种极至的美可以是一种幻觉。正如劳里(Lawry)所指出的:“对于男人们和当时这位小男孩来说,发现这位女人的真实姓名反过来使他们已经亲眼目睹的极至美消失殆尽”。只有那位成熟的男人发现了并且吸收了这位女人的两面性。读者被带入了几乎和叙述人相同的意识过程,和他一起去同另一种生命沟通。
故事中的现实渐渐地“熔合”,最后达到故事的结束,即自身“形式”的显现。这就是叙事者在故事末尾所说的“一件完整的事物有其自身的美”,更确切地说有其自身存在的价值。安德森在他的一封信中谈到了所谓的形式:“我觉得所有从事艺术实践的人都以不惜追求秩序为开始。我们想把某种东西带进意识中来,这种东西总是存在着,可又总是捉摸不到……我深信就形式而言,在很大程度上是个深层的感觉问题”。显然,只有创造该故事潜在意义的叙述人能体会到这种过程。正是通过这一过程,叙述人吸取了现实中的格里姆斯和她所象征的理想美的某些方面,他最后显露出自己是艺术家。这位躺在雪地里的女人在当时在场的男人们眼里成了“美丽的少女”。但毫无疑问,发现这个女人的身体并不是整个过程的结束,这种极至的美可以是一种幻觉。正如劳里(Lawry)所指出的:“对于男人们和当时这位小男孩来说,发现这位女人的真实姓名反过来使他们已经亲眼目睹的极至美消失殆尽”。只有那位成熟的男人发现了并且吸收了这位女人的两面性。读者被带入了几乎和叙述人相同的意识过程,和他一起去同另一种生命沟通。
![]() 如果接受肯尼迪的分析,我们会相信艺术和现实是相互独立的:艺术是人所创造的;现实是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大千世界。如果混淆不清,就等于没有分清什么是感性的和什么是被感知的对象;或什么是描述和什么是被描述的对象。虽然小说是真实生活的人为“重组”,是真实和想象的融合,是“半人半羊”,是根据作者的审美标准来安排秩序的,但小说并不保证其描述的内容是外在世界的真实反映。肯尼迪的观点并不完全是形而上学的。他忽视了现实的意义和其对人为的想象和重组所起的最有影响力的作用,但他毕竟意识到事实的存在和作用。事实上,元小说与人对外在世界的理解是密不可分的。它不是纯粹的技术性产物,它的生命在于现实生活,“林中之死”最终是关于生活的小说而不是“小说的小说”,尽管我们可以认为似乎只有小说本身在“说话”。文学艺术的现实主题总是存在着,不管它是被有意识还是无意识地创造出来的。故事中的精神升华被认为是“死”后的最后“实现”,而在现实生活中,“美”也可以以“死”而告终,或变成一种理念。这种理念可以存在下去,但也可以因为死去的是位老妇这一事实而荡然无存。事实上,不管极至的美是否在死后仍然存在,不管这是事实或是理念,这女人的身体和她的一生都在让读者作出判断。这决不是叙事人的感悟或是作者的想象所能左右的。现实和外在世界总是在说着话,在讲述着。在这里我们不是想去简单地否认小说作为一种隐喻有着自身创造的价值,也不否认叙述人的微弱和笨拙的表达反而使得故事推向了表达的高潮。但如果我们理解到拙笨不仅仅是叙事人的困惑,也是作者和读者的困惑,那么故事从事实发展到神秘,从回忆发展到想象这一过程本身就成了不可回避的现实。
如果接受肯尼迪的分析,我们会相信艺术和现实是相互独立的:艺术是人所创造的;现实是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大千世界。如果混淆不清,就等于没有分清什么是感性的和什么是被感知的对象;或什么是描述和什么是被描述的对象。虽然小说是真实生活的人为“重组”,是真实和想象的融合,是“半人半羊”,是根据作者的审美标准来安排秩序的,但小说并不保证其描述的内容是外在世界的真实反映。肯尼迪的观点并不完全是形而上学的。他忽视了现实的意义和其对人为的想象和重组所起的最有影响力的作用,但他毕竟意识到事实的存在和作用。事实上,元小说与人对外在世界的理解是密不可分的。它不是纯粹的技术性产物,它的生命在于现实生活,“林中之死”最终是关于生活的小说而不是“小说的小说”,尽管我们可以认为似乎只有小说本身在“说话”。文学艺术的现实主题总是存在着,不管它是被有意识还是无意识地创造出来的。故事中的精神升华被认为是“死”后的最后“实现”,而在现实生活中,“美”也可以以“死”而告终,或变成一种理念。这种理念可以存在下去,但也可以因为死去的是位老妇这一事实而荡然无存。事实上,不管极至的美是否在死后仍然存在,不管这是事实或是理念,这女人的身体和她的一生都在让读者作出判断。这决不是叙事人的感悟或是作者的想象所能左右的。现实和外在世界总是在说着话,在讲述着。在这里我们不是想去简单地否认小说作为一种隐喻有着自身创造的价值,也不否认叙述人的微弱和笨拙的表达反而使得故事推向了表达的高潮。但如果我们理解到拙笨不仅仅是叙事人的困惑,也是作者和读者的困惑,那么故事从事实发展到神秘,从回忆发展到想象这一过程本身就成了不可回避的现实。